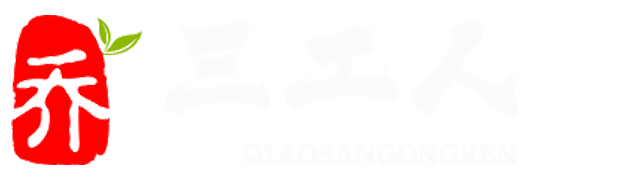个人自传可以写真实姓名吗(普通工人个人自传个人自传还可以这样写)
在我编辑湖州晚报“南太湖 纪事”版面时,接到过不少老年人的文章,大多是一些对过往岁月的回忆。接触了这个圈子后发现人在退休后,写个人回忆录似乎还挺流行的。董惠民60万字的《小写历史——一个普通人的六十年》,就在此列。

恰如其分的记录
大约在1972年。
董惠民在一篇名为《多瑙河之波之波》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终于盼到《多瑙河之波》在湖州上映,第一天晚上我放下饭碗便赶去人民电影院。只见同岑路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等候退票者居然站到路口的药店门前。人民电影院一般电影晚上安排两场,而《多瑙河之波》竟安排了三场。我去时第一场已在放映,而第二场是黄金时段,不可能有人退票,只能寄希望于晚上9:15时的第三场。企盼哪位兄弟怕睡得太晚影响次日早起,能割爱于我。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晚上9时刚过时等到一张退票。”
当看到这一段描写后,作为编辑,我毫不犹豫地决定刊登这篇文章。因为我的记忆深处也有《多瑙河之波》这一部反映二战的罗马尼亚电影,这部电影在当时轰动一时。不同的是,这部电影在湖州放映时,董惠民已经是湖州一家国企的工人,而我还是一名小学生。尽管如此,这部电影在当时的反响之大,在两个相差14岁的人中间都刻下了烙印。
我还记得那一句有名的台词,“安娜是个好姑娘,你要好好照顾她。”
“几天下来,厂里的青工大多看过此电影,甚至还有看上三遍四遍者。厂里无事闲聊,那几天七扯八牵总会提及此电影。那一句“安娜是个好姑娘,你要好好照顾她”,竟成为众青工挂在嘴边的警言,不说上几遍怕给人以落伍的印象。”
既然作者在文中也引用到这一句台词,我大笔一挥便将标题改成《安娜是个好姑娘》。
然而,在接到董惠民以后的几篇来稿后,我才发现,这个标题改得真不好。董惠民的回忆文章着重的是真实,是恰如其分的记录。
后来在阅读《小写历史》时,加深了这种印象。董惠民记述历史,取其小,不求于大。只重事实,不求华丽。这是作为历史学者,大学历史教授最可取的写作态度。虽然,这是一部有关个人的回忆录。但因他尊重事实的态度,反而使其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纪录。

在我们那个时代
也许和董惠民当过工人的经历有关,《小写历史》中的历史讲述,就像日常跟人聊天一样,平坦而又明确。
在《小写历史》第一篇“普陀山逃走一个小和尚”里,董惠民是这样告诉我们,其祖父“和尚”之名的来历。他说,
“祖父另有一小名叫‘和尚’。因为湖州有一种旧俗,若家有很珍贵的男孩(如独子),又担心他夭折,可起个贱名如阿猫、阿狗之类,如此便容易养大。”
不以尊者讳,这是董惠民与当下许多回忆文章不一样的地方,也是他的一个高明处。
当下的个人回忆录,在提及父母、祖父母等先人时,大多是歌颂的。然而,我认为对这些曾经来过这个叫地球的星球的生命来说,最好的纪念是记住本来的他。而不是被塑造出来的人物。
董惠民写自己也遵循着这样的原则。他的《小写历史》记录了自己“一个普通人的六十年”,“我”被贯穿于始终。然而,他的这个“我”在文章并不是最引人注目的。我的一个阅读体会是,《小写历史》的价值不在“我”,而在于“我”记录下的我们,我们那个时代。书中的那个“我”是普通的,甚至也是有普通人都有的种种不足,而“我”经过的那个时代,是伟大的,是丰富的,也是生动的。更是读者愿意关注,和应该被记住的。
《长大后我就成了我》 董惠民记录了自己在湖州书院30年的执教生涯。文中记录了学校的一段历史,也留下了时代的烙印——那个时候是这样的。比如那个时候,大学生恋爱还有“早恋”一说。
“至上世纪末,大学班主任工作中费力最多的是解决学生‘早恋’。”
董惠民写到:
“时间穿越到20年前,‘早恋’可是学校中的大忌。一旦发现班上有学生在恋爱,系领导、班主任、辅导员一齐出动,找男女双方谈话,从当代革命青年的远大理想、崇高职责,扯到家长培养之含辛茹苦、养育不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反正归根结底一句话——马上分手。若过上几日效果不甚明显,便使出最后的撒手锏——将男女双方家长叫至学校劝晓,只要做母亲的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诉几声,涉世不深的男孩女孩一般便会缴械投降。”
才20年前,在我们的高校中竟还有这样的事。谁能想到?
这便是修史的意义了,哪怕是小写的历史。

人一生就是一本书
董惠民1948年出生,经历过下放农村当农民,上调进厂做工人,他在恢复高考那一年考入大学,毕业后进入湖州的高等学府任教。可谓经历丰富。
他那一代人,因为时代的原因,大多有着各种各样的经历。当到得老年,很多人回忆自己的一生会发现:我的一生是可以写成一本书的。
董惠民说,个人自传的写作是一个思考的过程,从写作中学会理解,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理解别人也理解自己。在理解的同时,学会宽容。正如一位名人说的,有时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2009年退休后,董惠民继续留校任教。第二年,他动手《小写历史》的写作,三年时间他就写下了60多万文字。
《小写历史》的顺利成书,董惠民认为主要得益于自己一生“不舍得扔东西”的习惯。工厂的厂徽,学校的校徽,工作证,病历卡甚至是食堂的饭票,汽车轮船票,电影票,一切在别人眼里没有保留价值的东西,他却不舍得扔。有时,翻到一张旧饭票,一段记忆深处的往事就会浮现出来。成为《小写历史》的一个章节。
《小写历史》是按时间顺序排的,而董惠民在写作时,却是随意的。想起什么就写什么,在一个事件的写作中,又勾起了对另一件事的回忆,这样生发开来,就成了今天洋洋洒洒的样子了。
经一年修改后,《小写历史》于2016年3月出版。这部“以一个普通人生活中经历的犹豫彷徨、起伏沉浮,反映出整个时代的动荡变迁与发展进步。”的个人回忆录,成为当下个人回忆录写作热潮中的一朵浪花,开启了以小我反映大时代的写作路径。

《小写历史》后,董惠民循着自己的回忆思路,在“一个人普通人的六十年”中不断发现新的写作资源,产生新的想法,并把这一切付之笔下。本报在去年刊登的《安娜是个好姑娘》就是其中的一篇。董惠民向记者透露,他从每天两个多小时的写作中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享受到了人生的一大乐趣。把自己经历的事写下来,奉献给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和所处的时代。
包括收录了《安娜是个好姑娘》(《多瑙河之波之波》)一文的二三十万字的《小城故事》已付梓印刷,即将出版。

对董惠民来说,退休后,回忆峥嵘岁月,写写个人回忆录,不亦乐乎?

《小写历史》作者,董惠民。1948年11月3日出生。浙江省湖州市人。湖州师院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教授。2016年3月出版《小写历史——一个普通人的六十年》。
——本文配图均由董惠民先生提供

湖州晚报 编辑 柳自成

长按二维码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