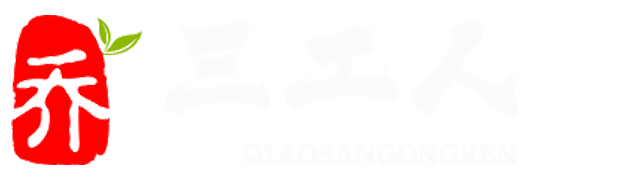利益分析方法的种类包括(帮派工人和普通工人利的分析)
每个人都是追求利的动物,每个人都在寻找对自己更有利的方式生存,这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的本能。
人从出生开始,受到父母的照顾和管束,并对他表示服从,是因为从父母那里得到了生存的条件,得到了食物、知识,以自由作为代价换取了生存和生活的利益,这种利益大于他独自的个人利益,所以孩子依赖父母,而当孩子逐渐长大,成人,面对社会时,他已不需要父母的照顾,他以自己自由为代价牺牲而换取的照顾被他以为的个人能够创造的独自生存的能力所代替,所以他渴望独立,渴望自我的意识和个性,这是因为他已有了独自的思考能力和生活能力,他的依赖性已不足以使他屈服,他的个人自由的利大于了他依赖父母所得到的利,所以他抗争,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他的认识是在不断的增长的,他对自己拥有和自己独立掌握的利的需求在逐渐的增加,事实上,在父母与孩子间就存在着这样一种利益关系,父母抚养孩子,孩子赡养父母,这是长久的一种利益关系,父母与孩子各取所需,父母对孩子前期的利益付出换取孩子将来对父母的赡养,而在前期实际上存在着这样一种利益关系,父母对孩子前期的照顾抚养与孩子自己自由给予父母的权利,孩子从刚出生当然不具备自由的权利,而当他逐渐长大,自我的意识和对自己权利的要求逐渐增加,但是他却还未能摆脱和需要父母的抚养时,这种隐性的利益关系就会出现冲突,造成孩子与父母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本质上就是利益矛盾,是父母抚养从而拥有的掌握孩子自由的利益与孩子自我权利争取的意识苏醒的利益的冲突,在这个时期,孩子本身是一种不成熟的状态,他还不知道他不具备独立和摆脱父母抚养的能力,他的自我的意识大于一切,而事实上这种意识并不能够帮他争取到他所能获得的最大利益,所以他是不成熟的,他的认识是肤浅的和自我意识是强烈的。这种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利益联系是短暂的,当孩子摆脱了父母的管束后,这种利益关系事实上已不复存在,而父母照顾孩子,孩子赡养父母的这一种利益关系却长期存在,直至父母与孩子一方死去,那么父母照顾孩子是为了孩子赡养父母,是有目的性的,但是又怎么保证孩子在不需要父母照顾以后一定会赡养父母呢?孩子的个利明显已经成熟,不需要再去赡养父母了,因为从父母那里他已经得不到利了,从另一个方面讲,父母照顾孩子,父母难道不担心利益的付出在孩子长大后没有利益回报吗?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利益关系了,但这时候孩子却不得不赡养父母,这同样是因为利,孩子从父母那里走向社会,从一个小的家庭环境面向社会,他受到社会的管束和控制,在中国,父母照顾孩子,孩子赡养父母一种传统道德,是基本的义务,孩子无法去与这种社会的秩序抗争,不然必将损害他自身更大的利益,损失他的诚信,他的名声,荣誉等等,以致他无法在社会立足,无法在社会中获利,在这两种利益的损害中,必然取其轻,所以他会履行对父母的赡养,而父母也能够去抚养孩子,因为他们能够得到利益的补偿。这种利益的分析,是相对于孩子与父母两方的,相对的简单,而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种利益的交换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一代一代人的更新补充,它是利于统治的,它对于孩子与父母两方都有照顾,都能够获得所需的利益,是相对公平的,这种利益交换在无数的家庭内部进行,家庭形成一个基本的权利单位,减少了社会的消耗和公共人力物力的输出,使社会层次凸显,有利于社会的治理,而这种社会的稳定同时也反馈给父母孩子的家庭小团体,使他们能够获得安全。
人从家庭到社会,同样是以获取他的个利为最优先原则的,从中国广大的外出打工者进行分析,打工者与企业进行利益的交换,打工者劳动,以劳动获取金钱,就是一种最普遍的利益交换,打工者出卖劳力提供商品给企业,而企业用商品进行销售获取金钱,再从金钱中取出一部分给予打工者,自留一部分为自己的利益,构成了一个基本的利益关系,打工者与企业主之间的利益关系,劳动-商品-售卖-金钱的利益分配,在利益交换的过程中,打工者与企业主各取所需,构成一种利益的平衡,而当打工者的劳动付出过多而他所获得的金钱却不匹配他的劳动,或是企业主为了自己能得到更多的利润而削减打工者工资的时候,又或是打工者的金钱太高引起企业主不满时,他们所构成的利益关系就会出现失衡,打工者和企业主的矛盾就会被凸显和爆发出来,无论是哪一方的利益受损,都势必影响到另一方,打工者利益受损,他就会抗争,就会消极怠工或是进行罢工活动,辞职等手段去损害企业主的利益,因为他的利益与企业主的利益在这个企业中即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他的活动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正常生产和发展,影响到企业主的收入,在利的关系中,利并不是一种单一的东西,它即是单一的一种个利,但同样它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利益,利与利之间构成联系和一种整体的利益群体,这种群体包括了打工者和企业主的个人利益,形成了一个共同体,打工者可以通过这个共同体影响企业主,企业主同样也可以通过这个共同体影响打工者,在企业中打工者不可能长期从事基础的简单的工作,打工者希望获得职位的上升和薪酬的增加,在企业内部,就与企业中的中层管理者和企业主发生利益关系,企业主需要考虑是否需要在原定管理者的基础上增加或减少管理者,对现有管理者进行提拔或辞退,对打工者进行提拔成管理者,而在中层管理者眼里打工者同样威胁了他们在企业中的管理地位,他们三者之间就会产生因为打工者自身希望获得更大利益的这种愿望而产生的冲突,因为这种打工者的个人愿望有可能损害中层管理者的利益,冲掉他的岗位,可能损害企业主的利益,制造新的管理者,而这种管理者也未必比原来的好,或者数量和质量的变化对企业产生新的不好的影响,他们三者之间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相互斗争,那么如果是这样,就会有一个疑问,难道处处都是利益的冲突和矛盾,难道一直的冲突下去无法解决吗?当然不是,上面说到,这三者的利益虽然相互牵扯和矛盾,但它们有一个特点,这些利益的冲突都存在于一个整体的企业中,这就为利益的调和和矛盾的缓和提供了解决的途径,因为利益与利益之间有共同存在的桥梁和联系,它们共同存在于企业的整体利益之中,如果打工者全部罢工,企业生产停滞,整个企业没有产品销售,整个企业的利益就会受损,企业主同样没有工资发放给打工者,打工者就得不到他想要的利益,还进一步损害了他自身的利益,企业如果倒闭,他将没有收入也没有了工作,同样,中层管理者如果打压打工者,不让他们晋升,或者拉小团体,结帮派,必然结怨与一般工人和打工者,打工者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同样不利于企业的生产,也不利于中层管理者的管理和他在企业中的发展,企业主也是一样,正是因为利益间存在着联系,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斗争和相互团结的这样一种特殊的关系,就为每个人都希望无限多的个利,不可调和的个利提供了调和和相互控制的基础,在企业主、中层管理者、打工者这三者个利之间,有着相互联系和相互调和的一面,有他们共同合作的一面,他们都属于一个企业整体利益的一面,所以他们之间可以相互妥协,进行个利的退让,这种利的退让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利益,而是为了他们争取更多的利益,利益的争取和追求是人永远不变的主旋律。
由企业中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进行努力和奋斗的,在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利益关系,而这种关系中必然蕴含冲突,但这种冲突是可以缓和的,因为在利益冲突中有着合作和利益的共同体,人可以为了个利而进行个利的退让,而这是为了更好的获得个利,是一种手段而已,它不是结果。
那从更大的角度,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是不是这样的呢?其实也是这样,国家的统治由很多的阶级、很多的层次构成,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相比较有着很大的变化,从统治者而言,最大的变化就是权力的缩小,从古代一言九鼎的皇帝到如今人民民主的领袖,古代的皇帝随口就能决定多少人的生死,但我们现在的领袖可以吗?难道我们的领袖不想拥有这样一种权力吗?人的追求就是个利,古代皇帝把这种个利可以说发挥到了极致,天下都是他的,那现代的领袖为什么就不能了呢?难道是他不想吗?不是的,而是他不能了,或者说他现在的不能就是对他个利最大的维护和帮助,这是因为时代在变化,世界在变化,社会民主和人人平等的观念普及,法制的普及,人民自身的权利是呈现出一种扩大的趋势的,老百姓的个利越来越大,权利越来越多,自然统治者的权利就会缩小和得到控制,统治者如果倒行逆施,老百姓是不会答应的,所以现在的统治者和老百姓间是一种新的利益关系,它不可能会到古代皇帝式的权威和权利了,强行行使,只会把自己的利消耗殆尽,拖入万丈深渊,而同样回到本质问题,统治者同样会追求他的利益的最大化,但这种追求不一定就是表现为他的权威或者权利了,这看似冲突,其实和企业主那个问题是一样的,他与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整体-国家,统治者与人民在利益联系中冲突,同样在利益冲突中缓和和退让,只是为了他的长远利益而牺牲掉短期利益罢了。
个人利益的获取是每个人生存和生活的最主要目的,无论是汲汲功名之辈还是隐居世外之人,都难逃利益的罗网,汲汲功名之辈希望做人上人,获取更大的利益,隐居世外之人有的是为了隐居的名声而隐居,等待时机出山来获得他的利益,有的是真的隐居,因为他想逃避,他的躲避现实麻痹自我亦或是求个自在清净,无论何种情况也是为了他的利,他的唯心的利益,他为他自己给自己设置的幻想中的利益而奋斗,仅此而已。一个生活在幻想与虚无中的人所追求的利是没有价值也没有意义的,它从本质上孤立于群利之中,孤立于社会之中,只存在于他一人心中,这种利益与无益无疑,这个人活着其实与他死了没什么区别,世界只有他一人,世界其实也没有他一人,他并不存在,已经消失,所以对这种唯心的个利,没有必要去讨论,但对于汲汲功名之辈的利益,是需要去思考的,个人利益的追求总会受到各种其他利益的影响,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存在于社会中,与其他人产生联系,我们的个利必然与其他人的利益产生冲突,这种冲突是显性的同样也是隐性的,显性在于个人与他直接产生联系的那个人或者那个群体之间,但是也有它隐性的一面,个人利益与他根本没有接触的社会其它层面的其它人或者组织的利益之间,这种利益的冲突是不直接的,但是它确实存在,它是隐性的一种利益冲突,关于隐性的利益冲突,需要详细解释一下,显性的利益冲突很好理解,它是显而易见的,就像上文中谈到的打工者、企业主之间,他们存在直接的利益关系,自然也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但是隐性的呢?从打工者而言,如果他与企业主的矛盾爆发,他采取消极怠工的方式进行抗争以争取他自己的利益,第一受影响的肯定是整个企业和企业主,但是在企业外部同样存在着很多的与企业相关的利益关系,比如说商品市场,比如说要购买企业商品的人,这些人和群体本身并不与打工者产生联系,但是因为打工者的消极怠工,产品生产不出来,他们的利益事实上也受到了影响,所以从本质上讲,他们的利益之间产生了联系,他们具备一种隐性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不是面对面的,直接的,而是隐藏的和间接性的,显然打工者的行为不光损害了企业主的利益,也损害了市场上这种商品销售者和购买者的利益,如果这种商品是一种出口商品呢?那更损害了出口贸易的利益,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所以为了个利而进行利益冲突的影响可以是小的,同样也可以是影响深远的,他不光是一个人个利的影响,在某些时候利益联系的牵扯中同样可以影响到大的集体的利益,不管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利益冲突,但是在冲突中有一点可以确信,利益与利益之间存在斗争,但是它们也相互妥协,妥协是为了更好的获得这种个利,我们在追求我们的个利的时候,需要多思考一下我们的利益在整体利益中是什么样的地位,我们为了争取利益的行为又会对整体的利益,以及我们的个利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这种整体可能是小的也可能是大的,这个个利间的牵扯可能是你我他,也可能是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因为个利的冲突中有它显性的一面同样也有它最容易被人忽略的隐性的一面,在你争取利益的同时,做什么样的行为,用什么样的方式,是暂时的让利还是积极的争取,是激进的行为还是缓和的妥协?让自己的个利与其他人的个利与群利间真正的统一起来,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中让自己能够获得真正的,最大的,最有价值的个利,我想,这才是每个人真正在社会中拼搏和获取利益的方式。
在争取利益的过程中,是需要遵守一些契约和原则的,它们是奠定人类社会的基础和基石,它对于争取利的过程有着规范和引导的作用,像上文提到的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利益关系,只不过把它规范化和标准化形成了对利益关系规范的准则罢了,比如歹徒为了利益伤害他人生命,他自己也要受到惩罚,这样一种法律法规的束缚,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利益关系,杀人偿命,杀人者被法律杀死,杀人者获得了杀死人的利益,而被杀者由于他无力杀杀他的人,由法律代他执行,其实就是利益的一种极端的交换,只不过这种利益交换的结果是以生命为代价罢了,法律保障了个人利益的稳定,保障了统治者利益的稳定,法律是从许多的利益关系以及利益关系中产生的冲突和交换中提炼和升华出来的,对各种利益关系中的冲突交换进行约束,道德准则也是如此,在强调一方的时候,另一方其实也被隐含在其中,因为他们是一个利益关系的整体,在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国家之间或是多种层次之间进行的利益交换中进行相对公平的判决和分配,维护利益交换的稳定和整个社会的稳定,道德和法律起到这样一种宏观的利益关系中的稳定作用,是利益关系中冲突与交换的标准。
在利的关系中有着冲突和妥协,它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取自身最大的利益,这点毋庸置疑,但是很多时候是事与愿违的,采取的方式和行动不符合最终个利的获取,反而损害了最终个利的利益,用主客观的观点来表示就是主观的行动并不符合客观事实规律的发展,在行动的过程中忽略了显性利益冲突和隐性利益冲突的存在和相互的影响,所以我们争取利益的过程中,是应该注意这点的,也应该有一个原则的,就是去力求达到一种状态,利的和合状态,个利群利国利乃至世界利益之间,能否寻找到一个平衡点,综合的去考虑利益问题,争取获得自己真正的最大利益,它应该是一种循环往复然而又螺旋上升的趋势,而不是一种单一的上升或单一的下降,这是需要深思和求索的。
这篇文章主要是从个人,特别是从平民的观点来论述平民对待利益的问题的,虽然平民与统治者之间在对待利益问题的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获得个人的最大利益,但是平民和统治者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那就是权力的不同,平民更多的只拥有自我的权力,而在很多时候,自我的权力也未必能够拥有,而统治者不同,他们掌握着控制他人的权力,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他们的影响力无疑更为广阔,这使得平民与统治者虽然在追求利益的目的上是一致的,但是他们追求利益的手段和方法,他们在追求利益过程中对整个利益体产生的影响截然不同,所以统治者的利益获取显然是更加复杂和牵涉众多的,对于统治者利益,还有包括许多人构成的大型的集团利益,是需要去另外分析的,平民在客观上具有他的局限性,而统治者的思想和权力显然是丰富和广阔的,他们拥有着更大的能力,更多的权威去获取他们的利益。